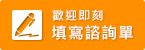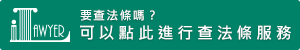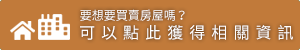日治時期強徵土地是否可以討回?
問題摘要:
日治時期遭非法徵收或未補償即列為國有之土地,是否可討回,須視個案證據情況詳加判斷。訴訟途徑為現行制度下唯一可行方式,人民應備妥相關歷史資料、契據文書與其他憑證,並針對登記瑕疵與財產權受侵害情形完整說明。憲法、民法與土地法所構築之法制體系,雖設有登記、時效等制度維護法律秩序與交易安全,但仍應回歸憲法保障財產權之初衷,避免國家因歷史與程序失誤,坐享人民應有之財產。如能提出足夠證據證明該土地原為自家所有,且為日治時期強徵或登記瑕疵所致,則返還之訴將有憲法與法律支持,訴訟勝敗關鍵仍在證據之充分與時空背景之說明合理性。
律師回答:
關於這個問題,日治時期遭日本政府強行徵收的土地,是否能在今日向中華民國政府請求返還,涉及諸多法律與憲政層面的複雜問題,尤其牽涉到土地權利的起源證明、國家責任的承繼、登記效力的性質、民法消滅時效制度的適用與否,以及憲法對財產權的保障。
首先,主張返還土地的人民須提出當時該筆土地為自己祖先所有的證據,例如日治時期的土地台帳、登記簿、土地契約書、納稅憑證等,以證明土地原為私有,至如何於戰後遺失所有權,例如在總登記期間未能完成申報或換發憑證,致遭登記為國有。
若此筆土地目前登記為國有,且人民主張仍為真正所有人,即可考慮提起「塗銷登記」之民事訴訟,請求國家返還該土地,惟需審慎處理訴訟策略與證據佈局。中華民國政府雖為日治時期政權之繼承者之一,但對於日本政府當時之行政行為是否須概括承擔責任,並非毫無爭議。
日治時期為人民所有,嗣因逾土地總登記期限,未登記為人民所有,致登記為國有且持續至今之土地,在人民基於該土地所有人地位,請求國家塗銷登記時,無民法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311號民事判例關於「……系爭土地如尚未依吾國法令登記為被上訴人所有,而登記為國有後,迄今已經過15年,被上訴人請求塗銷此項國有登記,上訴人既有時效完成拒絕給付之抗辯,被上訴人之請求,自屬無從准許。」部分,不符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112年憲判字第20號)
實務上,「登記絕對效力」,僅係保護基於登記而信賴取得土地權利之善意第三人,並不影響真正權利人對登記名義人主張物上請求權。即若土地尚未為他人所善意取得,原所有權人仍可對現登記名義人請求塗銷登記,返還土地。不僅如此,民法第759條之1亦明定,土地登記僅具推定效力,而不具絕對效力。
按關於土地登記之效力,土地法第43條固明定:「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然我國實務一貫見解,認此規定係為保護因信賴登記取得土地權利之第三人而設,並無於保護交易安全必要限度外,剝奪真正權利人權利之意,在第三人未取得土地權利前,真正權利人對於登記名義人自仍得主張之(司法院院字第1919號、第1956號解釋、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1892號民事判決先例參照)。98年1月23日修正公布之民法第759條之1規定亦依此見解,而明定:「(第1項)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第2項)因信賴不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律行為為物權變動之登記者,其變動之效力,不因原登記物權之不實而受影響。」。(112年憲判字第20號)
按消滅時效制度,乃權利人在一定期間內未行使其請求權者,義務人於該期間屆滿後,得拒絕給付之制度。消滅時效制度之立法理由,在於考量法律關係經過一定時間後,可能面臨權利人或義務人證據滅失、舉證不易、真實難辨,導致訴訟上徒增滋擾。立法者遂藉由消滅時效制度,使客觀上已繼續存在一段時間之事實狀態取代真正法律關係之認定,俾權利義務狀態不明之情況得以早日確定,以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惟民法之消滅時效,立法者雖賦予義務人得對罹於時效之請求權為拒絕給付之抗辯,但該權利並不因罹於時效而消滅,是義務人仍為履行之給付者,不得以不知時效為由,請求返還(民法第144條規定)。此外,為免權利人與義務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因義務人行使時效抗辯權而過度失衡或違反公平正義,行使時效抗辯權,應符合民法第148條規定,依誠實信用方法為之,且不得有權利濫用情事。準此,消滅時效制度之設計,絕非僅單方面考量義務人現有法律狀態利益之維護,而應兼顧權利人之利益,避免於個案中發生權利義務顯失公平之情事。…憲法第143條第1項規定:「中華民國領土內之土地屬於國民全體。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應受法律保障與限制……」;又「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為民法第758條第1項、第759條分別明定。…戰後初期所實施之土地總登記,雖為政府在政權移轉後管理國土、推行不動產物權登記制度所需,然該措施僅係確認、整理及清查當時土地之地籍狀態與產權歸屬,以利後續政令之推行,並無使不動產物權發生變動之意,非屬上開民法第758條第1項、第759條之情形。又,土地法第43條所定依該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僅為保護善意第三人因信賴既有登記而更為登記者,賦與登記之公信力,並非否認日治時期土地台帳或土地登記簿上所記載權利之效力。是日治時期屬人民私有之土地,雖經辦理土地總登記之程序而登記為國有,然該登記與物權之歸屬無關,並未影響人民自日治時期已取得之土地所有權,人民仍為該土地之真正所有人,此亦為審判實務上一貫見解(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1360號、80年度台上字第540號、85年度台上字第2466號、94年度台上字第834號、101年度台上字第1226號、112年度台上字第398號等民事判決參照)…國家基於公權力主體地位行使統治高權,致與人民發生財產權爭執時,國家本非憲法第15條財產權保障之主體,從而不生基本權衝突之情事。且考量臺灣因政權更迭而辦理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及換發土地權利書狀,當時之時空環境,絕大多數人民未通曉中文、因戰事流離他所、遺失土地權利憑證,或因社會資訊、教育尚非發達,不諳法令,甚至因36年間之228事件引發社會動盪等特殊原因,致未於限期內申報權利憑證繳驗,或於申報後未依限補繳證件,終致其所有之土地被登記為國有。於此情形,若使國家仍得主張民法消滅時效,從而透過時效制度維持私有土地登記為國有之狀態,不僅與誠實信用原則有違,且形成國家對人民財產權之侵害。故在憲法上,人民財產權之保障,相較於逕行承認土地登記為國有之狀態,更具值得保護之價值。是容許國家在此主張消滅時效,並無正當性可言。(112年憲判字第20號)
由是可知,土地登記本身僅具有推定權利歸屬之效力,不能作為認定權利取得或消滅之絕對依據。是當土地所有權之登記與真實權利狀態不一致時,真正所有人為回復其權利之圓滿狀態,原則上仍得對登記名義人行使物上請求權,而請求塗銷登記及返還土地。此權利具財產上價值,自應受憲法第15條財產權之保障。
法院往往會審酌當時徵收行為是否依法,是否補償,及是否於戰後總登記程序中合理維護人民財產權利。若日本政府徵收行為係違法、無補償,且人民未及於總登記完成權利維護,則中華民國政府承繼該筆土地的登記狀態,是否應負財產權侵害責任,必須依據具體個案事實判斷。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而日治時期依法取得的私有土地,在戰後不應因行政登記的變化而喪失實體權利。
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應受法律保障與限制。此等規範綜合表明,在無信賴利益介入之情況下,真正權利人對登記名義人之物上請求,仍有其憲法及法律之正當性基礎。另就民法上之消滅時效制度,雖原則上權利人若於一定期間內未行使其請求權,義務人得主張拒絕給付之抗辯,但該制度設計仍應符合誠實信用原則,並防止權利濫用。
日治時期土地若因逾期未登記而被登記為國有者,於人民主張所有權並請求塗銷登記時,應不適用民法消滅時效規定。此一解釋明確指出,人民原有之土地權利,在因戰後時局混亂、語言不通、教育程度有限等客觀因素下未能完成登記,國家若仍主張時效抗辯,形同坐收不當利益,違反憲法第15條保障財產權之意旨與民法第148條誠信原則。
土地總登記制度原為確立土地權屬、推行土地政策所設,並非創設或消滅權利之機制。換言之,登記行為並非物權變動之本質依據,未登記並不當然喪失權利。此亦與民法第758條規定相符,僅於基於法律行為之物權變動,始須登記生效,若為繼承、判決、徵收等非法律行為取得者,則應於事後辦理登記,始得處分,惟取得事實並不因未登記而無效。
國家若因政權更迭或登記程序瑕疵,而取得本應屬於人民之土地所有權,於人民有充分歷史與法律依據主張其權利時,國家主張消滅時效、拒絕返還,應屬違憲且不符公平正義。土地為人民生存之基礎,財產權屬基本人權核心內涵,在國家未能舉證土地已依法取得、或有合理補償之前,單憑國有登記,不足以推翻人民私有之主張。是以,人民如能提出日治時期權屬證明、並證明土地徵收程序違法或未補償,即便已登記為國有,仍有機會透過民事訴訟請求塗銷登記。縱使案件涉及史實久遠、證據蒐集困難,若人民能說明時空背景、無法取得登記資料之原因,並提出可資佐證之文件與證人證言,法院仍可能依實質正義原則予以認定。
房地-土地徵收
瀏覽次數:3